| 看扬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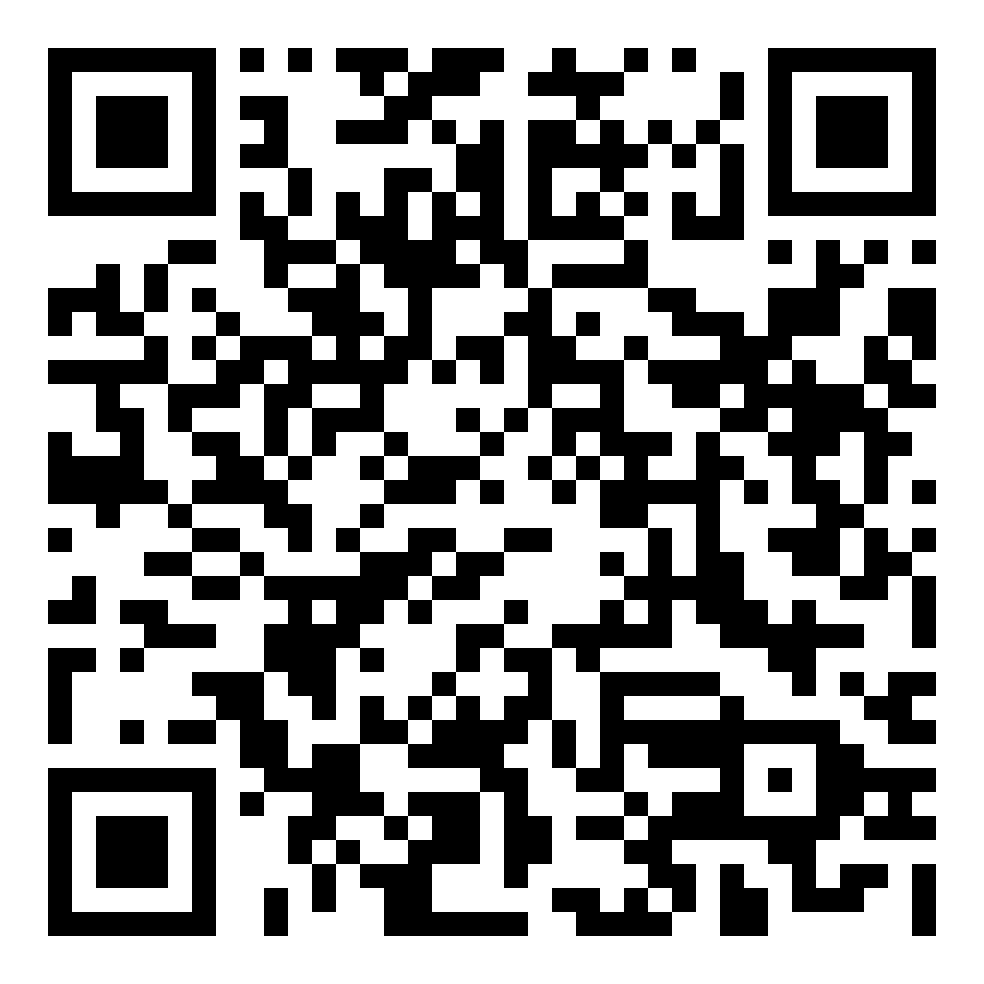 |
| |
 |
滚动播报 |
|
 |
头条新闻 |
|
 |
扬中要闻 |
|
 |
综合新闻 |
|
 |
社会民生 |
|
 |
热线 |
|
 |
江洲论坛 |
|
 |
公告公示 |
|
 |
专题特稿 |
|
 |
影像扬中 |
|
 |
视听在线 |
|
 |
图闻扬中 |
|
 |
文苑 |
|
 |
健康 |
|
 |
关注 |
|
 |
风采 |
|
 |
媒眼看扬中 |
|
|
 |
|
|
 |
文苑 |
|
|
| |
|
□ 范选华
2024年即将过去。这一年,于我来说,有点流年不利。因为这一年有段时间,我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跑医院,让我心生许多无奈,有时还有很重的无力感,甚至被绝望笼罩。跑医院,有时却也能让我感受到别样的温情,顿悟出些许的生活哲理。
(一)
小舅离开我们已有月余。他走之前的那段时光,我能做的唯有陪伴,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家里。
在中医院簇新的住院大楼里陪伴小舅时,我总是喜欢透过窗子望着落日的余晖。那如血的残阳,有时是那么沉重,有时又会让我觉得温暖。正如这医院,进进出出那么多人,有人在这里经历着病痛、折磨与死亡,也有人在这里得到了拯救重启人生,更有许多的新生命在这里呱呱坠地拥抱世间。
其实,在医院我们看到的就是生命的进程,在医院我们能够悟到,生老病死就是一个个鲜活的我们必须直面的人生。
小舅走了,走得有点匆忙,有点决绝。他曾跟我抱怨过,与其这样耗着,不如早点离开。他也曾尝试着早点离开,但都被我劝退了。其实,对于生与死如何抉择,我也是无知的,更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如今,每次踏入医院,心中还会生出这样的幻想,假如我们自己哪天罹患重症倒在了病榻之上,苟且延续生命时,该怎么抉择?是顽强对抗病魔,然后一天天枯槁下去,直到周身插满管子,丧失起码的尊严?我不忍!是放弃那根本救不了命的治疗,带着最后的微笑与傲娇体面地离去?我也不舍!
其实,在那样的一个时间点上,究竟是选择苟延残喘还是体面离开,需要的不仅是理性,还要有更大的勇气。因为面对死亡而谈论死亡,对于有着“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样文化基因的我们来说,如何对待生命,那是很艰难的抉择。
(二)
居家养老的姨娘八十开外,两个儿子英年早逝,遇到生病作痛找得最多的是我和姐。
炎夏某日,姨娘打来电话,开口就是“宝宝,老姨娘要死了”。放下手中的事赶去乡下,姨娘是病了,病得还不轻,腰腿不能动弹。赶紧联系医生,驱车到医院开始项目繁多的检查。拿着检查结果,推着轮椅上的老人找到骨科主任,这主任一开口便让人心生好感。老人说,这小伢和气呢。后来,“和气的小伢”主任亲自为姨娘做了骨水泥手术。不过他告诉我,老人年纪大了,骨折恢复虽慢但没大问题,大问题出在她脊椎管狭窄变形,解决“腰腿疼”、下不了地的问题,恐怕还要做大手术。
做大手术,是件大事,我不敢贸然决策。老人倒是爽气,手术肯定要做,问我能不能请个大医院的专家。
那天,我请来了大医院的专家,老人与专家面对面坐着,我在边上当“翻译”,老人的扬中话专家听起来颇为吃力。尽管如此,他神情专注,听得认真,问得仔细,然后提出方案,又耐心地解释。整个问诊,谈笑风生,如沐春风。老人说:“这个专家没得架子,看样子有点本事呢,交给他我放心。”老人手术很顺利,回家后感觉也不错,前些时候我去看她,她还到菜田里弄了一大把大蒜给我。
佝偻老人的笑容告诉我,医者仁心。我一向以为,这世上两类人最值得敬佩与尊重,一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还有就是与生死打交道的医者。每一次深思熟虑的判断,每一次精确无误的诊断,每一次耐心细致的问诊,都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他们脸上的凝重和认真,是赢得病人信任和安心的最重砝码。
有他们在,生活中,即使病痛缠身,我们依然有坚强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三)
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从不肯进医院、做体检的姐夫感到不舒服,医院检查有问题,但弄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去上海成了我们解决问题的首选,于是我们开始了上海的寻医之路。
扬中人聪慧好学,在上海许多顶级医院都有扬中籍的医生,好多还是专家教授。去上海寻医问药,先要找“扬中人”。只有“扬中人”,才能帮你预约各类检查,预约专家门诊,预约手术安排。
去医院问诊那天,前期工作做得相对圆满的我还是起了个大早,五点不到就和外甥女婿去医院门诊大厅排队挂号。
走进大厅,人头攒动。这些从祖国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有的拖着行李箱,操着一口地方方言,神情慌张地跟同行的人交代着什么;有的一手怀抱婴儿,一手牵着稍大点的孩子,不停地嘱咐着大孩子不要乱跑,生怕顾此失彼跑丢了娃;还有的满面风霜,低头一遍又一遍地翻查手中的资料,就怕有所遗漏;还有个年轻人转着经筒,嘴里念念有词,听不出念的是心经还是啥经……这些不远万里挤进这个顶级医院的人们,就像湍急河流里树叶上晃荡的蚂蚁,拖着危重的病体,抱着最大的希望,感受着最深的无助!
我混在这些人当中,一个跟着一个小心翼翼地排着队,生怕被后面的人抢了先。因为大家都知道,来一趟这里是多么地不容易,那即将要挂到的专家号,是我们亲人生存下来的最大希望。
好不容易挂上号,姐夫跟我们一起上楼去排专家门诊,从早上七点等到下午一点,终于排队屏上出现了我们熟悉的名字。饥肠辘辘、疲乏不堪的我们坐在了专家面前,专家简单地翻了翻检查资料,“这个毛病扬中也可以看,你们还是回扬中去看吧。再说上海靶向药都是集采的,还没有进口药,江苏说不定有”。
看着笑容可亲的专家,我心里不禁嘀咕,“这么简单啊,我们不远百里、起个大早、饿了老半天,等来的就这句话啊”。我看看身边的姐夫,他倒是满脸的释然,或许这正是他要的结果。因为,接下来我们不需要再像今天这样排队住院、排队手术了,回扬中又何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是啊,我们来“中国看病中心”,不就想要个安心、要个结果吗?否则,那么多人拖着奄奄病躯辗转千里,翻山涉水,历经艰辛,在这陌生的繁华都市里经受着诸多从未遇到过的难处和不如意,又图个什么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