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扬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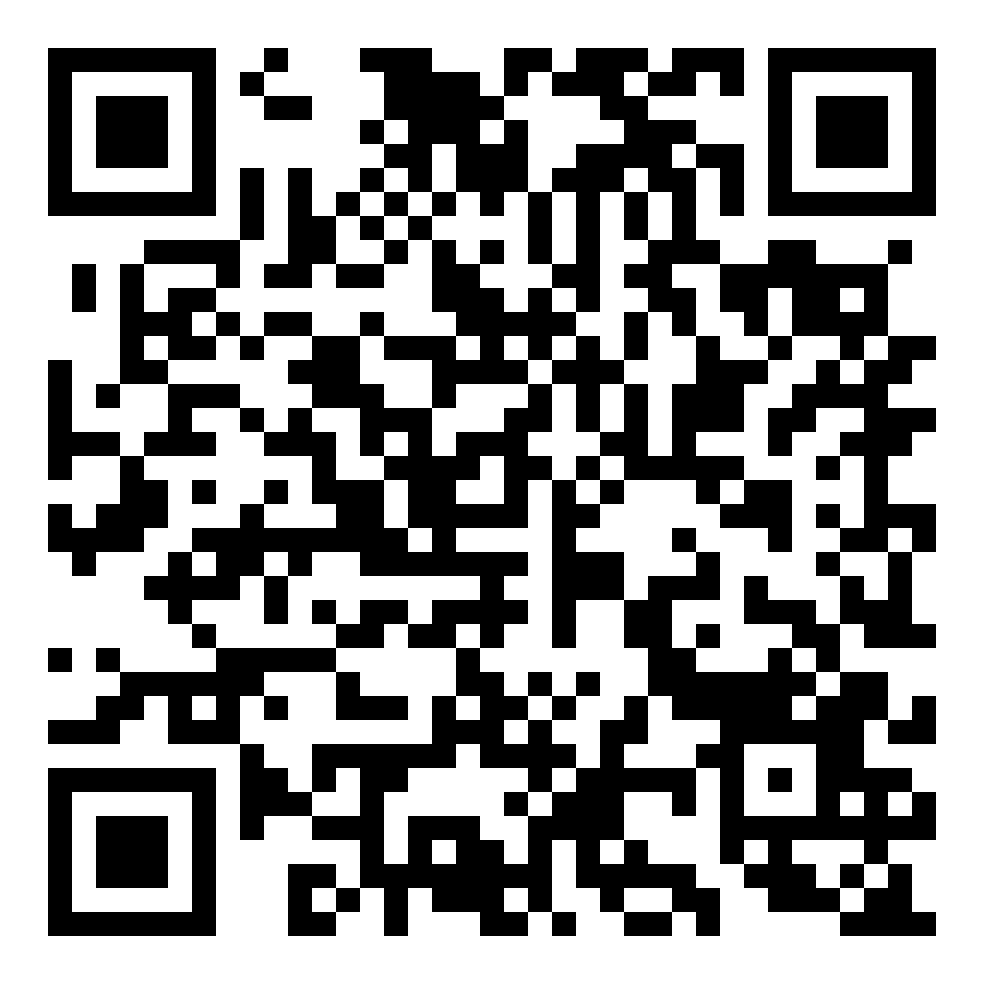 |
| |
 |
滚动播报 |
|
 |
头条新闻 |
|
 |
扬中要闻 |
|
 |
综合新闻 |
|
 |
社会民生 |
|
 |
热线 |
|
 |
江洲论坛 |
|
 |
公告公示 |
|
 |
专题特稿 |
|
 |
影像扬中 |
|
 |
视听在线 |
|
 |
图闻扬中 |
|
 |
文苑 |
|
 |
健康 |
|
 |
关注 |
|
 |
风采 |
|
 |
媒眼看扬中 |
|
|
 |
|
|
 |
文苑 |
|
|
| |
|
□ 陈锡余
近日,我翻书时发现里面夹着一份请柬,仔细一看,原来是1993年扬中县营房港小学成立六十周年邀请函。营小,在我县教育史上具有光荣业绩,系我县闻名遐迩的高小学府之一。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年时光。看着邀请函,拾起那些往日的片段,虽已暮色苍茫,不再少年,却忘不了当年记忆。
三茅街道营房村东侧,有条南北走向的港道称谓营房港,营小位于港的中段西侧,坐西朝东,有一约四丈的木桥与港岸相接。它创建于1933年,校址系清朝顺治年间世袭驻镇江京口八旗派兵到太平洲德兴洲(今三茅街道丰裕地区)北部营房村建立“生计所”。所谓“生计所”是指保障清兵及其家人粮草生活的后勤保障之地,很快建造了营房(又称庄房)。占地数10亩,周围有近3丈宽,5尺多深的壕沟,整个营房四面环水,但在东南角还有个几十平米的荷花塘,到了夏季盛开的荷花散发独特的清香。民国年间,常驻京口的旗人还仍然派人来扬收租(后收为公产)。我家还保留了一份民国14年(公元1925年)丹徒旗籍生计所发的租地执照 (已赠市博物馆)。
在我就读营小期间,所见房屋是前后三进,大概九架梁的瓦屋共九间,前排中间为通道,南北两侧各为炊事房和女教师宿舍;第二进,北为教师办公间,南为教室;第三进,北侧为教室,南侧为男教师宿舍。南北两侧均有门通往外面,整个校区可封闭。我记得依二、三进的南侧墙外还有数间教室,中间有天井,东头有个小门通操场。就在门旁与第二进墙的相接处有棵数丈高的椿树,树上有只视为智慧象征的猫头鹰窝。每当我们早晨做操时,它睁着眼睛看着我们,好似羡慕。
营房小学,曾先后更名营房港中心小学、五七学校,七十年代教育改革时,曾设有初、高中班。黄寿年、张大恒曾同时在该校负责和任教,后于1998年在丰裕镇建立丰裕中心小学。
营小创办人陆锦芳是位意志坚强、教学严谨、有正义感的校长。创办初期面对困难,他剃掉长发誓言办不好学绝不留发。他事必躬亲,我记得刚学写大字时,他为我写了一张“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的样品给我临摹。他亲自主持早操,为教导学生不要偷懒,不要恋床,还编了顺口溜:“早睡早起身体好,天天做早操”“说起就起,富贵到底”“说爬就爬富贵荣华……”他上课严肃,要求学生聚精会神听讲,对课堂提问答不上来的便施以戒尺,由自己打手掌。他是个正义感强的人,记得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急需补充兵员,经常下乡抓壮丁,附近一青年为躲避被抓,到营小以学生身份和我们一起听课。也可能是走漏消息,没过几天匪三民乡乡公所派兵闯入学校,将这一青年强行带走。匪政府的行为激起了师生的愤怒,当即他带领全校师生步行数里路去匪乡公所请愿。后迫于社会压力,很快释放了那位青年。
刚解放不久,人民政府派来了一位新任校长丁雄魁,丁校长是从苏北老区来扬的,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记得他曾教我们一首歌,歌词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幸福,人民政府爱人民啦……”当时,我这个刚10岁出头的孩童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了初步了解。我还记得解放前就到营小任教的仓道洲老师,他多才多艺,写字、图画、音乐都不错,平时言语不多,但搞宣传却十分活跃。在刚解放的几年,他常带领我们到农村人员较为集中的地方以唱歌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记得有年初冬到临近江边的原革新村宣传,其中一首歌是宣传扫盲的,歌词大意是:“寒冬腊月大雪花儿飘,人民政府实在好,到处办冬学……”还有宣传自由婚姻的,什么“强扭的瓜不甜”。
在营小上学期间,我也受到了“善”的教育,至今印象十分深刻。营小四周环水,唯有一座桥可进出。这座桥就是原上海大孚橡胶厂徐中和先生捐赠的。桥系木结构,全长15米左右,宽约2米,四周有护栏,中间系活动板可收可放。解放前曾见过他和夫人到过营小,并带来了慰问金,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他关心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我们吃过他发放的牛奶。我的印象是:牛奶是固体的,如同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石头,凡是在校学生每人一份,回去用开水一冲即可喝,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牛奶的味道。
在营小期间,我初步接受了儒家思想教育、善和恶的教育以及爱党爱政府的教育,使我在上学之余积极参加反霸、防特、站岗放哨能所能及的社会活动。
时间到了1952年,我小学毕业进入了初中,1955年于扬中县初级中学毕业(扬中尚无高中)。鉴于当时师资缺乏,且全民文化水平不高的状况,相当部分毕业生安排了工作,有的去了包头钢铁厂,有的当了小学教师。我接到教育科通知后随即到县报到,随后来到我的母校营房港中心小学任教(营小更名)。当时月工资26.11元 (按工资分计算),这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仅靠母亲种田,无其他来源)。我记得当时群众的生活水平仍很低下,有的学生无钱交学费便由学生家摊饭,以老师工资抵扣。
1956年我响应党的号召应征入伍,义无反顾地走上从军之路。我在中心校虽待了一年不到,曾先后负责一、二年级,但和学生建立了深厚感情,当我离校时人人送上了最珍贵的礼物——红领巾,我至今还忘不了那恋恋不舍的场面。时序更替,几十年后,我在路上偶遇到一些学生,我已忘掉了他们昔日的面孔和姓名,但他们仍能认出我,亲切地喊我一声“陈老师”,我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当一名人民教师真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