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地专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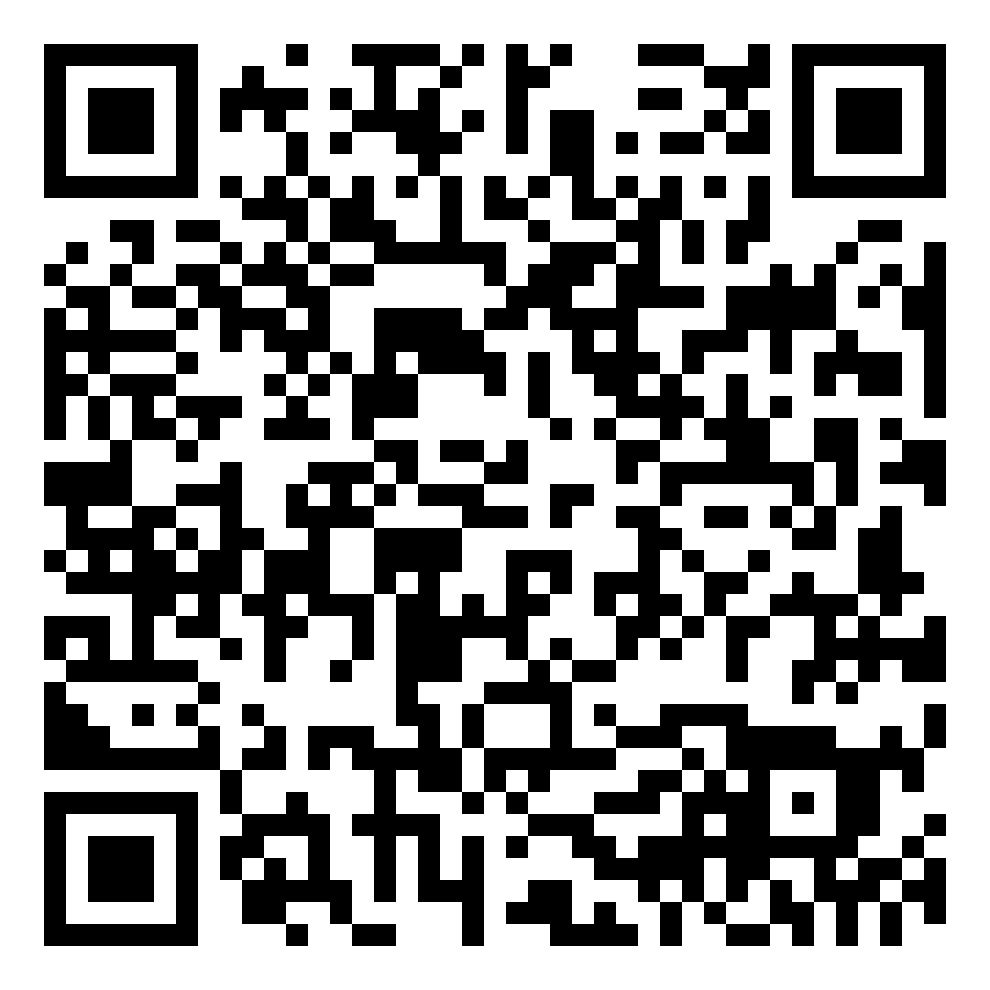 |
| |
 |
人大专栏 |
|
 |
政协专栏 |
|
 |
法治扬中 |
|
 |
扬中人医 |
|
 |
党员承诺 |
|
 |
党建工作 |
|
 |
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 |
|
|
 |
|
|
 |
人大专栏 |
|
|
| |
|
□ 范选华
上世纪七十年代过来的人,大多记得灶屋间里的水缸。在通自来水之前,扬中人大都是吃河水,河水用“量(liàng)子”(扬中话,意为挑水的木桶)挑家来,倒进水缸里,加进明矾沉淀后即可用来煮饭做菜烧水了。因此,水缸是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一代人生活的见证。
记得我家灶间的水缸是青褐色的陶制品,差不多有八十公分高,缸口直径一米五左右,上宽下窄肚子大,缸口有一圈凸起并加厚的粗陶缸沿,父亲说这对缸体有加固的作用。缸体虽粗粝却不失光泽,辅之以简单的条纹,看起来中规中矩。缸内表面光滑圆润,涂有一层深褐色的薄薄釉面,依稀能够照得见人影子。水缸的质朴无华与农家人的粗茶淡饭倒是很搭。
扬中人家水缸大多放置在大灶旁的墙边上,用两块半圆木板盖住缸口,上面放着一只水瓢,两只挑水用的“量子”及扁担水钩都整齐地挂在水缸的边上。水缸放在灶间主要有两个用途。首先自然是为了用水的方便,水缸挨着大灶,无需挪步,仅需转个身就能从水缸里舀上水来,省时省力。而灶间放置水缸,其实还个功用,就是防火。灶间是生火煮饭的地方,自然堆放有柴草,必须防止火“特”(扬中话,意为“掉”)出来。俗话说“穷灶门富水缸”,意思就是灶门前的柴草要少,水缸里的水要满,一旦发生意外,缸里的水就可以发挥大用场。
当年家里挑水用的 “量子”是请我们生产队“杨家埭”上一个姓汤的箍桶匠用“杉木板”做的,高约七十公分,内径五十公分左右,“量子”上下扎了两道铁箍,以防散板漏水。木制水桶虽用起来十分轻巧方便,但时间一长,木头会烂穿,铁箍也会生锈。因而在箍新桶的时候,箍桶匠都要先用油灰仔细填抹缝隙,再用桐油反复油上几遍。每次挑水过后还要把桶倒过来沥干里面的水,放在太阳底下晒晒,防止“量子”烂掉。
挑水是大人们的事。清晨,家家户户河边的水桥上除了洗衣服的女人,再有的就是挑水的男人了。那啪嗒啪嗒的捶衣声,咯吱咯吱的扁担声,哗啦哗啦的倒水声组成了乡间独有的“清晨序曲”。
当“人有扁担长”的时候,我们自然地承担起了挑水的重任。清晰记得第一次挑水时,我心有成竹地挑上两只“量子”,一摇一晃地来到水桥上,学着父亲扁担不离肩,用“量子”直接“捥水”。不曾想,这“捥水”是个技术活,怎么也无法将两只“量子”一下头捥满,只好老老实实把扁担卸下肩,一只量子捥好了再捥另一只,然后,才歪着肩膀“甲”(扬中话,意为佝偻)着腰把两只装得不太满的水桶摇摇晃晃地挑回家,一路上,量子里的水也不知道洒出来了多少。
家里的水缸不大,一般挑上三四担就能盛满。但毕竟一家人的生活用水都在这只缸里,所以,每隔两三天,就要再挑上一次。水缸满后,母亲总要用菜刀在砧板上敲下一小块明矾放到缸里,一会儿功夫,原先稍显浑浊的河水,就会慢慢地变得清澈起来。
为了使缸里的水保持洁净,母亲还请箍桶匠顺便为水缸配了两个半圆对开的水缸盖,防止“堂灰”屑子或者苍蝇蚊子掉进缸里。每次挑水前,趁缸里存水不多时,母亲都要将水缸彻底清洗一遍,用“洗锅把子”一遍又一遍扫除沉淀在缸底和四周缸壁上的污垢,再用铜勺把清洗的污水一勺一勺舀出来,最后还要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
用过水缸的孩子都能记得水缸这个简单的物什给我们带来的别样快乐。寒冷冬日,灶间的水缸里也会结上一层薄薄的冰,早晨起来需要用水,先要用铜勺把冰敲碎。喜欢玩冰的我们就会不失时机地捞上一块放在手里不停地玩弄,任冰块“神奇”地变成水滴。还可以站在火热的锅膛边上,在烟火氤氲中用嘴轻轻地像吮棒冰那样吮着冰块,却有一番“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意境。
水缸很质朴,但也很神奇,因为水缸会“出汗”。春夏时节,当水缸外表开始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珠”时,大人就会说,天要作变了。上初中物理课方知,因为快下雨的时候空气里的湿度较大,而水缸水面以下部分的温度相对较低,水蒸气遇冷后就会凝结成小水珠附着在水缸上,形成水缸“出汗”的现象。
在那生活贫乏的年代里,水缸不仅给农家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给懵懂的孩子们提供了探索奥秘、寻找乐趣的条件。几名比缸才高出半个头来的孩子围在一只空水缸边上,只听那“叽哩呱啦”的声音在耳边“嗡嗡”作响,说话声越大里面的“嗡嗡”声也越大,很是好玩。大了以后所学的物理知识告诉我们,原来是“声音共鸣”在作“怪”。
水缸与大灶为邻,一家老少的平常日子就从这里开始。只要缸里有水,锅膛里就不会熄火,日子就不会停止。天长日久,一口小小的水缸,却盛满了清清浅浅的光阴,记录着岁月流转的沧桑。女人作为灶间的主角,每天围着灶头、水缸、饭桌忙前忙后,却总不忘对着水缸中的影子整理一番自己的妆容,醮一抹清水梳理下稍显凌乱的发丝。在外面“皮”累了的孩子跑回家,第一时间是冲到水缸边,抓起铜勺“咕咚”一下舀出一勺清水,一仰脖子将水灌进肚子,一勺水下肚的瞬间带走了所有的饥渴与炎热。有时候大人们发现菜刀不快了,那粗糙无釉的缸沿就成了“天然”便捷的磨刀石,只要把菜刀放在缸沿上别一别,钝了的菜刀马上就锋利许多。
时过境迁,关于水缸的一切离我们越来越远。而对于我来说,那曾经承载沧桑过往的青褐水缸,不仅装满了父母的汗水和辛劳,也装满了生命的延续和渴望,更装满了悠长的人生记忆和淡淡的乡愁哀伤。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