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扬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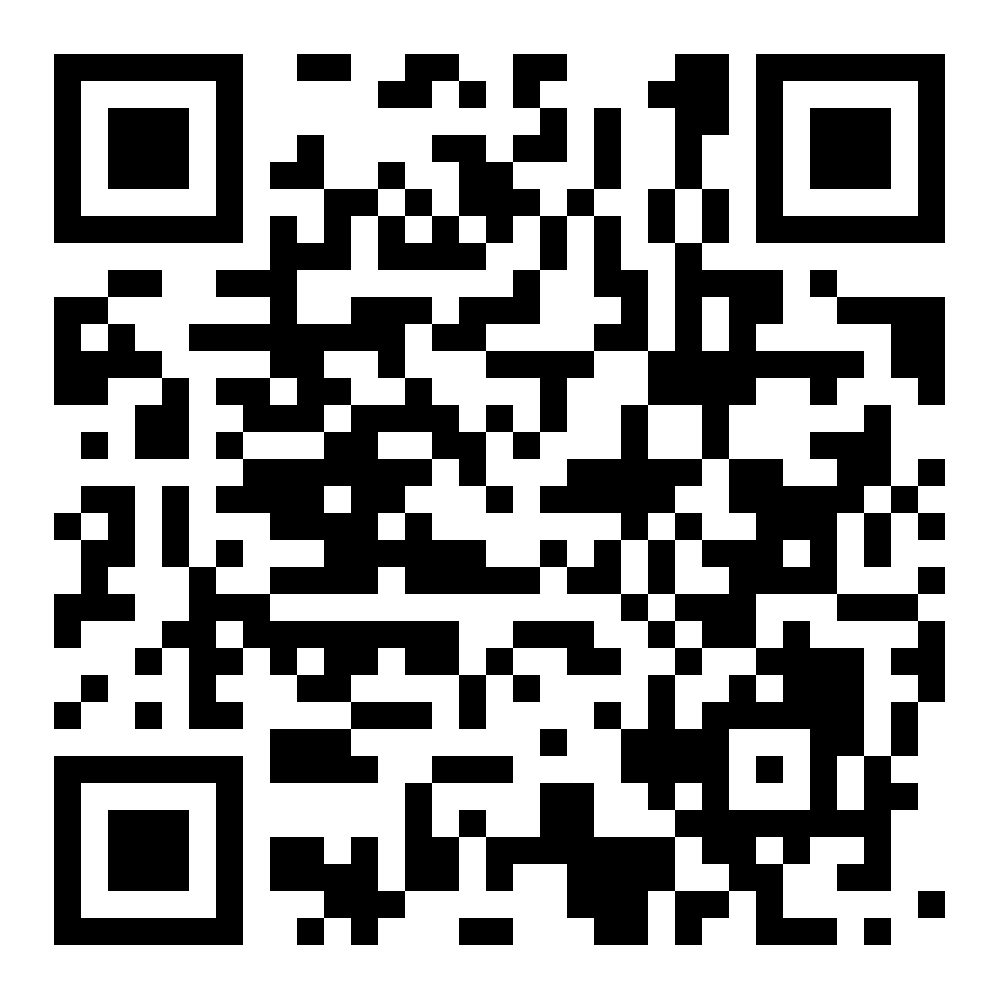 |
| |
 |
滚动播报 |
|
 |
头条新闻 |
|
 |
扬中要闻 |
|
 |
综合新闻 |
|
 |
社会民生 |
|
 |
热线 |
|
 |
江洲论坛 |
|
 |
公告公示 |
|
 |
专题特稿 |
|
 |
影像扬中 |
|
 |
视听在线 |
|
 |
图闻扬中 |
|
 |
文苑 |
|
 |
健康 |
|
 |
关注 |
|
 |
风采 |
|
 |
媒眼看扬中 |
|
|
 |
|
|
 |
文苑 |
|
|
| |
|
□ 倪昌国
我自幼在镇江读书,师范毕业后又在丹阳工作了16年,每次回扬中,或乘姚镇班,或在栏杆桥渡口摆渡。坐姚镇班,站到接的划子(小船)上,或摆渡的船在码头靠岸,想的是“回到家乡了”。再顺了新坝大港的堤岸,前行约两华里,经栏杆桥,过拐弯处。在北方约百米处,一座高高大大的建筑,青砖黛瓦,两排风火墙(墙垛子)如苍鹰展开的双翅,凌空欲飞,这时想的是“到家了”。这样的情绪只有盼望回家的游子才能体会到。
门楼有4米多高,虽没有砖雕,但显得简约大气,也是一种美吧。门口铺着两块长长的青条石,厚厚的形成了不高的台阶。青石的门槛,两扇大门是实木拼成的。迈过门槛,大门里是个门厅,约半间房子大小,有梁有柱,但三面是空的。两边铺的花岗石,北面铺的青石,中间铺了砖。三个天井,中间是方青石铺的,两边的天井铺的是乱砖瓦。
房屋的主体是一排五间七架梁敞步檐的建筑。中间是堂屋,老三份共有,祭祖、办喜事都在这里。北墙中间陈放着供桌,当中是香炉,两头各有一只花瓶,悬挂着一幅中堂,是人物画,两旁是对联。是何人所画,对联是何人书写,写的什么,当时年龄尚小,均不知道。供桌前摆着一张八仙桌,两旁各有一张太师椅,桌沿和椅背均刻有花纹。1954年夏的水灾,家里的水深近2米。那年我在镇江初中毕业参加中考,到春节回家时堂屋里的字画等均不见了。堂屋两边的房间,房门相对,在南侧。每间房屋均用木板相隔,面对走廊一面也是,称板壁。这两个房间因为有两扇对开的窗子是木格子的,可能因为光线较好的缘故,当时叫“明间”。东西两侧的房间没有窗户,门对着厢屋。两个包厢五架梁,屋脊比正屋要低一点。对外的一面有板壁,有窗户。正屋和厢房都有走廊,边沿铺的是磨光的长方形青条石,里面铺的是青砖。正屋和厢屋中间是个过道,东西各有一个边门,实木的。厢屋的山墙向内是围墙,近4米高,中间便是大门了。
与这四合院成直角,东侧有五架梁楞摊瓦屋三间,前沿强与四合院山墙相平,距离约三米,半段墙是砖砌的,上面是土垡的。
正屋东西还有三架梁楞摊瓦房三间,南北走向,南山墙与正屋围墙相齐,也是半段墙为砖砌,上面是土垡砌的。正屋西面还有草屋两间。
这座五间两包厢的四合院和东侧三间与围墙成直角的房屋是曾祖父倪国钧在清末建造的。晚清咸丰年间高祖父倪学林和兄弟倪学宽等在泗阳经商,起初小本经营,后来逐步做大,到同治年间,在泗阳竟有 “倪半城”之称(即开的酱园、糟坊、商店等几乎占了半个城,当时泗阳也是个小县城)。高祖倪学林去世,他的长子倪国钧(我的曾祖父)成了 “掌门人”。然而这个“家族企业”中“学”字辈和“国”字辈中多人染上了吸鸦片烟的恶习,传说有“13支枪”(鸦片烟枪),整天吞云吐雾,不思进取,搞得家业败落。倪国钧虽已届而立之年,但无力驾驭,于是他决定放弃“掌门”的地位,分了家。
他把自己这一份换成银两回扬中,在栏杆桥和福星桥之间,新坝大港东侧(现永平村17组)买了四、五十亩地,占有一个小圩。建了个四合院,多余的木料和砖瓦等又在东侧建起楞摊瓦三间。住宅前有河塘后有沟,房屋和河塘之间是菜地和场。河塘的四周栽了杨树,河塘东边是坝头,开始有用竹枝编成的门楼,有竹门,拴上便不能通行。西面是新坝大港,港岸内是竹园。竹园外港岸内侧栽的全是长满刺的树 (我们叫它“炸针树”),并用竹子扎成厚的篱笆状,人是无法通过的。正屋后也是竹园,竹园后有一条宽约4米的河沟向东延伸,与东边钱姓住宅后的河塘相连。三间楞摊瓦房的东侧,与钱姓宅基地之间是一块桑园,一亩左右。两姓之间的分界处也有篱笆相隔。这就是曾祖父建的一座小庄园。他在世时雇两三名长工,过忙时再请些短工,过着“小地主”的生活。
到了我的祖父,这一辈有兄弟三人,成年以后分家成了三份。祖父是长子,分了东面正屋两间和东厢房,他后来又在东山墙外建了楞摊瓦房三间。这三间最北隔了猪圈养猪,猪圈外堆放柴草摆放农具。当中一间较宽敞,东面的窗户较大,是一块块木板插在槽子里,把一块块木板下掉,外面则一览无余。放上八仙桌、长板凳,一家可坐着吃饭。最南面砌着灶台,大小两个锅。夏天坐在弄堂里特别凉快。这三间屋1954年水灾倒塌了,没有重建。
二房叔祖父倪思武分得西面一个明间和院子外楞摊瓦屋。三房叔祖父倪思贵分了最西一个房间和西厢屋,可能是因为他继承了倪国钧三弟倪国安 (无子嗣)的财产。他将正屋给儿子住,在正屋西山墙外建了两间草屋老夫妻俩住。
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5月我的父亲倪凤奎牺牲在战场。祖父倪思文原在泗阳经商,并担任泗阳县商会会长,泗阳即将沦陷时他回到老家扬中。1938年9月,母亲带着刚满月的我也来到扬中。1939年党派张日化(县委组织部长)、陆钧(新坝区区长)来新坝区开展工作,在我家落脚。祖父安排他们住在东厢屋,那里是我的叔叔倪有道住的地方,有床,有桌凳。祖父和他们畅谈天下大事,分析抗战形势。
张日化同志牺牲后,1941年党组织又派张建新(区委书记)、刘震东(区长)、刘晓阳(军事助理)等来新坝区工作,也经常食宿在我家。由于父亲的影响,张日化、张建新等同志的教育,我叔叔倪有道,姑母倪兰英和倪菊英,母亲倪建民先后入了党,成立了新坝第一个党支部,张建新兼任支部书记。他们开会、讨论问题,就在与正屋相隔一条弄堂东面的楞摊瓦房里——我们一家吃饭的地方,那里有桌子、凳子,既方便也比较安静、安全。
在我家的老屋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1944年腊月的一天夜里,汉奸顾秉琪的侦缉队包围了我家,抓走了我的祖父倪思文。这些汉奸就是一帮土匪,在我家翻箱倒柜,把准备过年的东西抢劫一空。母亲坐在床上,把我抱在怀里,《前进报》和一些宣传材料贴胸藏着才未被发现。1946年春节后,国民党反动派先是抓走了我的祖母,是夏景元放了她。后来又抓走我的叔叔倪有道,是和尚庄房的永清和尚去保回来的。不久的一天,母亲发现特务殷其红在大港对面走来走去,母亲和我匆匆吃了点菜粥,收拾了点换洗衣物,在栏杆桥渡口过江,此后便在镇江读书,又在丹阳工作,只有春节或者假期回家了。
我家的老屋,晚清时代的建筑,很有特色的四合院,抗战时期上洲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应该说很有纪念意义。原址距238省道仅200多米,如果保留下来,建个新坝抗战纪念馆再合适不过了。可惜1983年拆除了,几个本家住户要这块宅基地和房屋上的材料建新房。当时我也没有这个意识,即使有也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把这座老屋买下来。
我已是85岁的老人,谨以此文为老屋留下记忆,兼以缅怀在新坝地区工作战斗后来牺牲的张日化、张建新、刘震东、刘晓阳诸烈士!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