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扬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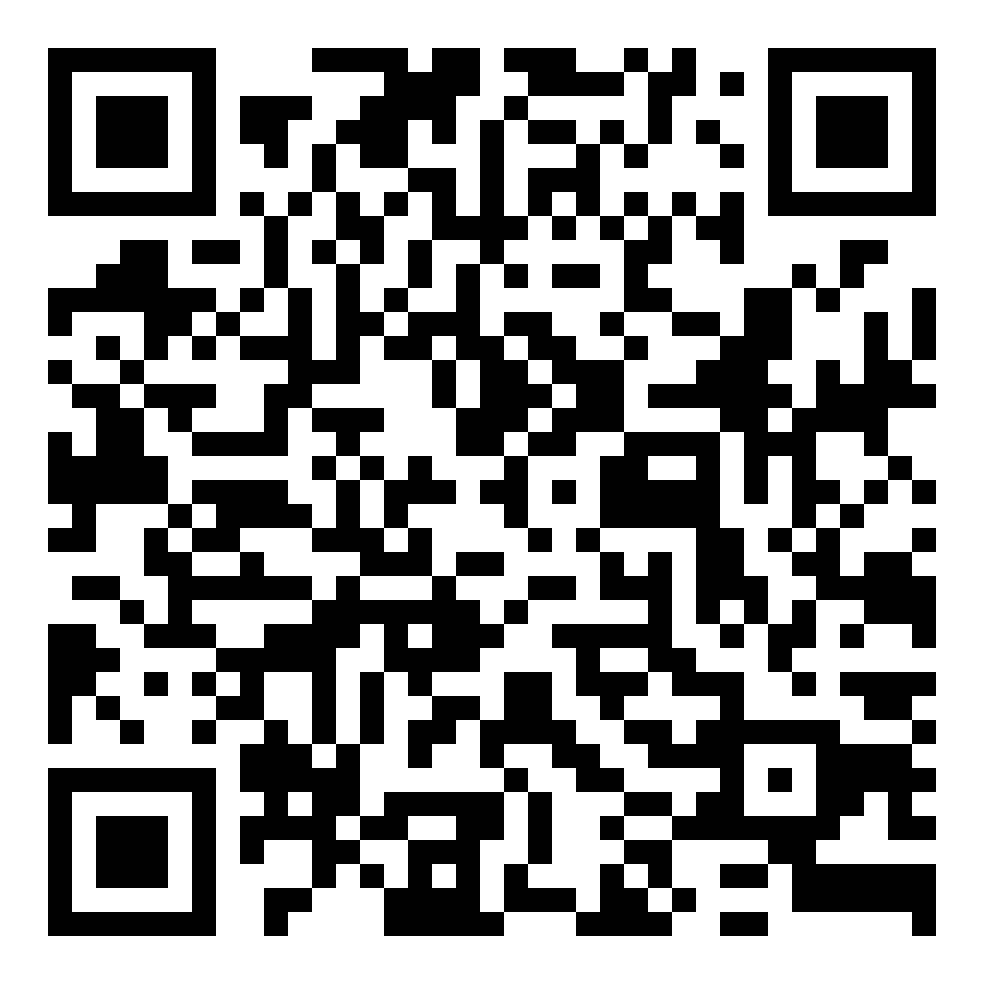 |
| |
 |
滚动播报 |
|
 |
头条新闻 |
|
 |
扬中要闻 |
|
 |
综合新闻 |
|
 |
社会民生 |
|
 |
热线 |
|
 |
江洲论坛 |
|
 |
公告公示 |
|
 |
专题特稿 |
|
 |
影像扬中 |
|
 |
视听在线 |
|
 |
图闻扬中 |
|
 |
文苑 |
|
 |
健康 |
|
 |
关注 |
|
 |
风采 |
|
 |
媒眼看扬中 |
|
|
 |
|
|
 |
热线 |
|
|
| |
|
建安的本名非常诗情画意,美得像只存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小说里。
说起“建安”这个名字,可是引经据典得来。小学六年级时,他不晓得从哪里弄来一本讲述“建安文学”的著作,好像是图书馆的弃书,还是在旧书摊老板推荐下购来的,总之他与那本书一拍即合。那厚重的书页里躲着密如蝼蚁的文字,一段话尚未读完,就被艰涩的笔调弄得反胃。但建安却读得津津有味。
他天天捧着那本书,学古人摇头晃脑地背诵。有时听他说几句王灿的赋,倒也有模有样,感觉肚子里藏着不少墨水。不过建安却也读出了一个怪毛病。某次我提到钟嵘《诗品》评论曹操的诗“其古直而少文采”,因而列为下品。建安竟怒不可遏地大骂:“钟嵘算什么东西!他根本不通文墨!”接着又劈里啪啦地骂了一大串,但建安压根儿不知道钟嵘是谁。
初始几次,我以为建安是在说玩笑话,但这样的举动做多了,便发现不太对劲,而且他的举止愈来愈偏激。升上高一时,有同学讽刺“孔融让梨”是沽名钓誉的行为。本来这只是博君一笑的戏言,谁都没料到竟引爆建安的理智线,他发狂如台风肆虐,把整间教室掀得像废墟,还追着那同学一直跑到教研室寻求庇护。事情结束后,建安被贴上异类的标签,鲜少人敢再与他攀谈,他成了班上的绝缘体,吸收一切孤寂。建安却自诩隐士,以此为荣,他宁可陪晨光晚霞私语,也不愿在俗人身上浪费唇舌。他对建安文学的着迷已近固执,曾在语文老师面前将被喻为曹植接班人的杜子美评得一文不值。
在他眼中“建安”年号以降的朝代是一片文化沙漠,那些骚人墨客都是不入流的文盲,那么辉映于七子之前的大文豪们呢?全被建安归类成尚在钻木取火的北京猿人。他除了当起建安文学守护者外,索性连名字都改成“建安”,不许任何人提及他原先的姓名,诸多怪异的举动仿佛在跟以前的自己划清界线。
弹指数年,建安就像换了个人似地,将自己牢牢封闭,他的身体里好像住着另一个古老的意识。这样的巨变愈演愈烈,他任赤草爬满成绩单,成天游魂似地流浪。老师的谆谆告诫,全淹没在他迷惘的漩涡里。
毕业时我们造访一胜地,山岚笼罩满山,缥缈中不知有何绝景。这景色大概激起建安归隐的绮想,在这地方他格外安宁,像要融入幽美山景之中。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忽然他吟着王灿的《登楼赋》,像唱京剧一样纵气奔腾,萧萧寒风如北管激昂的曲调。建安看起来就像发着呓语的狂人。陌生的游客因好奇而伫足,彼此交头接耳,但窸窣蜚语穿不破他悲亢的语词。
此情景令我联想到《镜花缘》,唐敖跟唐闺臣登上小蓬莱,联结前尘的记忆。倏然我脑内闪过一个画面,那是建安敞开双手纵身跳下悬崖。我赶紧上前要抓住他,但他只是轻轻一叹,便缓缓走下山。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方才的吟诵宛若海市蜃楼。
毕业前夕,我邀搪塞多次的建安来家中与同学相聚。一阵酒酣耳热后,建安忽然号啕起来,问我为何七子要抛下他。泪声俱下的哭诉令人怅然。恍惚间,建安像在对辽阔的天地呼号,想唤来同类,但转过身来,广袤的尘世里仅余他孤独只影。他站在天台对远方发愣,风将他羸弱的躯体吹得嘎嘎作响,似乎随时会崩化。
为了不让他继续忧悒,我也带他去接触过不同的兴趣,希望能催醒他萎靡的灵魂。但他沉得像一艘搁浅许久的船只,已被侵蚀得面目全非。“人生几何?”是建安最常自问的一句话,但一手一手的啤酒只是让酒精加速腐化他的身躯。
若能招来孔融或谁的魂,或许便可得知建安是否在那杳渺的时代流连忘返;假如能托这些英魂带回口信,冀望他们能告诉建安,二十一世纪才是他所属的现实,兵马倥偬的王朝已是远古的梦。人生须有两副痛泪: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然而建安的文友知己存在久远之前的时空,怎么盼也盼不到了。
毕业后我负笈至外地求学,尚未上轨道的生活使我无暇追踪建安的近况。直到去了他坟前上香,脱离高中生涯不过半年。一个生命忽然消逝,一切发展得太过突然。搜不到遗书,查不到遗言,建安用力割断手腕动脉后抱着那本“建安文学”睡着,了结缠绵六年的闹剧。
他终于挣脱枷锁,飞往魂牵梦萦的桃花源。可惜我仍招不来王粲、孔融等人的魂魄,只能胡乱勾勒建安欢愉的景象,并偷偷把中国文学史里的“建安七子”划为八子。
□ 菜丛
|
|





